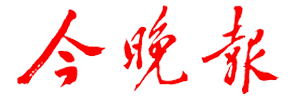我喜欢爬山,盖因在山乡长大。小时想,山外边是什么?爬上驴脖子山,群山在视野尽头层层叠叠地绵延向远方。
那段栖居泰山脚下的岁月里,我踏遍了周遭的每座小山,就连巍峨的泰山主峰也早已被我征服。少年时仅用两小时便能登顶的矫健,如今已化作整日攀爬主峰后的气喘吁吁。岁月流逝,昔日的少年玩伴不少已离世,唯有泰山依旧巍然矗立。
我有一位来自泰山后石坞的好友,他在铁路系统工作。当年他从铁路工程队考入南方高校后,曾给我写过好几封洋洋洒洒十几页的长信,信中我们约定暑假一定要回泰安一起爬山。那个暑假,山里的核桃树结满青果,我俩蹲在溪边掀开山涧里的石头。小溪的石头下有螃蟹,有小虾,还有赤鳞鱼。在泰山古老的传说中,夏日置赤鳞鱼于岩石上,经烈日曝晒可以化油而流。那年,我俩捉了一条赤鳞鱼,想看看那鱼儿是否真能被太阳晒化。
后来我俩像铁路线上的两个车站,互相打探着对方的消息,一晃三十多年没有见面。那天与他通话,才知他现在住在济南,后石坞是回不去了。乡亲们大多去了泰城。他说,他也受不了泰山夏天的蚊子和冬天的寒冷。城市让我俩蜕变成一棵弱不禁风的草。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写过一篇小说《我是一条赤鳞鱼》,主人公是一条游荡在泰城的赤鳞鱼。那种意象,如今想来仍闪烁着少年的光亮。
那是怎样的一种经历?儿时春日,我总追着青草的气息奔向山脚。那时的泰山脚下还铺展着舒缓的开阔地,宛若雄浑乐章前的轻柔序曲,让人窥见泰山的可敬与俊美。如今这些开阔地,早已被密密麻麻的住宅楼侵占。人是自然美的最大破坏者。人们赞美着泰山,却又无时不在毁坏着泰山上的一切。和原生态的泰山相比,今天的泰山早已面目全非了。因此,我格外钟爱泰山周边那些未经雕琢的小山。
我曾无数次攀登过那些小山,曾在夏日炎炎里,沿着山中小道行走,知了声刺破山林的寂静。在人迹罕至的山中,松树是陌生的,泰山石是陌生的,荆棘也是陌生的。某次无路可行,我硬着头皮攀岩而上,谁知肚皮被锋利的石尖划破了,四野无人可以呼救,只回荡着知了的嘲笑。负了轻伤的我挣扎着爬到山顶,在那座小山上,竟有篮球场一样大的平坦山地。我躺在两树之间的吊床上休息,山风推着我轻轻摇晃,好像整个山色都属于我。那片平坦的山顶,我后来寻觅了几次都没有找到。因为泰山上未经开发的地方,景色大多相似。我拼命在记忆中搜寻,却再也找不回那个夏日里珍贵的清凉,徒留肚皮上一道伤痕。每次看到它,我都能回忆起那个难忘的夏天。那晚,我独自在山林里过夜,只挂了一张吊床。四周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,奇怪的是,我竟丝毫不觉得害怕。那时的自己,身上还带着青春的朝气。如今这把老骨头,怕是再没勇气独自留在山上了。
秋天的小山最有趣,人越少的地方,山果越多,有山楂、柿子、松子还有山枣。摘一把红果子塞进嘴里,真甜。秋意渐浓的小山上,蚱蜢的腿脚不再矫健,知了的嗓音也染上沙哑,连大黄蜂都显出几分倦怠。偶有蝴蝶掠过,翅上亦沾满岁月的霜色。我常独坐小山山顶,看群峦如臣,拱卫着泰山主峰。秋风过处,山色日渐清朗——脚下公路似玉带轻悬,铁道如长鞭远引。
最难忘冬天飞雪时爬山的场景。上山时雪打在脸上,寒风刺骨中夹杂着雪花融化的温热。当我终于小心翼翼地攀至峰顶,脸上的积雪已化作泪珠般晶莹的水滴。我是上午沿着雪路往上爬,下山途中,我打起十二分精神,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谨慎。积雪已深,皑皑白雪中唯有万松挺立,那浓郁的苍翠灼灼地映照着双眼。古时的樵夫也会在雪天登山吗?奔跑的野兔此刻也躲起来了吧?雪把整个山都封住了,像一个远行者给门扉贴上了白色的封条。走到山下,我长舒一口气,不禁惊叹自己的壮举:怎么上去的?又是怎么下来的?我的天!
今天的我,离原始的泰山越来越远了。我怀念泰山,更怀念泰山周围的小山。它们曾给予我最温暖的记忆片段,如清泉般滋润过我的心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