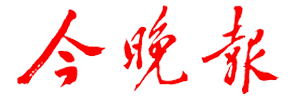重读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跟随她进入临死前那种痛苦和幻灭的境地,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次死亡。“她两手着地扑到车厢下面,微微动了动,仿佛立刻想站起来,但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就在这一刹那,她对自己的行动大吃一惊。‘我这是在哪里?我这是在做什么?为了什么呀?’她想站起来,闪开身子,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,从她背上轧过。”火车仿佛也轰隆隆地从我的背上碾过,把我变成了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据说福楼拜曾说“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”,对于因杰作而进入作品人物内心、全身心地去体验另一种人生的读者来说,这句话同样可以成立。法国文学专家袁筱一曾指出,这句话其实是给福楼拜写传记的一位作家假借福楼拜之口写出来的,未必实有其事。但袁筱一认为,不管有没有这句话,《包法利夫人》的主题很明确,它阐述了一种心灵的状态,即人类有能力,并且总是要把自己想象成另外的模样,它邀请我们思考我们和真实之间的关系。袁筱一关于小说主题的概括,同样适用于我们阅读小说时可以抱持的一种角度,即借此想象另一个自我、另一种人生,并且思考自己与真实之间的关系。包法利夫人和安娜·卡列尼娜,都是超越时代、国界与性别的,是“我”,是“我们”。
如果安娜生活在今天——如果我就是安娜,我能逃脱这宿命般的不幸吗?如今,人们似乎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爱情与婚姻,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人生。安娜所面临的不能离婚的困境,应该可以摆脱。但人生的困境,并不会因此而消失。真正令安娜绝望的,是爱情——某种不可定义、不能定形的激情的消逝。那激情曾经唤醒了她隐藏在平静生活下不可扼杀的生机,却无可挽回地消逝了。准确地说,在她这里,并未消逝,反而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加剧、蔓延、变形,最终吞噬了她。而在伏伦斯基那里,却变成了冷漠、厌倦,最终成为一种负担、一种不得不尽的责任与义务,而这对高傲而敏感的安娜来说,却是莫大的侮辱。
安娜最终将自己的人生孤注一掷地投入爱情,而在信仰、事业、家庭,其他种种提供情感支撑的人际关系方面,她却几乎已经一无所有。她像一个将要溺亡的人抓住救命稻草般抓住伏伦斯基,这当然是徒劳的,她只能跟这根稻草一起,沉入黑暗而冰凉的水底。
将生命的全部寄托在爱情上,这固然是非常危险的,因为人生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倾倒的倒金字塔。那么,如果生命中又有爱情,又有信仰、事业、家庭等各种支撑,是否就能构成一个稳固安全的正金字塔?如果还是只有一种支撑,那么把爱情换成信仰或事业等,那个倒金字塔是否可以扩大底座而成为稳定的四方体?就像生物多样性能够支撑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,人生的丰富性,或许也能更好地支撑起幸福的人生。尽管在哲学家那里,“幸福”如何定义又如何获得,都如此困难而复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