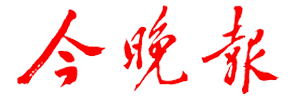家乡平谷,盛产白薯。天快冷了时,农人们便三五成群地把自留地的白薯一趟趟运回家。白薯不便于露天贮藏,必须放入井(农人自己挖的一种用于储藏东西的窖)里,或生切晾干,或蒸熟晾干。
那年白薯产量过盛,于是家家户户都在为白薯忙活。生切晾干有两个用途:一是做饲料,二是漏白薯粉。而蒸熟的白薯,要切成橘子瓣状,端到房上晾干,等冬春两季时给孩子吃,也可以送人。家乡的房子是青瓦房,非常适合晾干。于是,农家的房顶上便出现了一片片红白相间的白薯干,极像一次盛大的农展会。红的是红瓤的白薯,白的则是白瓤的白薯。
那时,家乡人以吃粗粮为主,白薯亦是上好的口粮。所以,绝大多数的白薯都要窖藏起来。奶奶家的院子里早就挖好了一口井,几米深,下去后一拐弯,掏一个洞,几百斤、上千斤的白薯都要运进去,一直吃到开春。窖藏的白薯经过一个冬天的沉淀,逐渐流失水分,口感变得格外好,因此才显得特别珍贵。农人们舍不得吃,便到集上去卖,换成钱贴补日子。
晾生白薯干最省事,只需在地上铺一领苇席,或摆在窗台上晾晒就行。麻雀是熟白薯干的天敌,如果它们铺天盖地而来,白薯干就会被啄得只剩一层皮。这时,农人们或在烟囱上绑个破草帽,或在房顶立个稻草人,或让红绸带随风飘荡在房顶,以吓唬麻雀,但这也免不了白薯干遭殃。最有效的办法是人轰,拿一面铜锣一阵敲击,既惊得它们魂飞天外,也能让它们消停好几天。
暮秋时节,房顶就是天然的展台。悠长的瓦沟里,黑红相间,农人们用白薯干做标点,诠释岁月的艰辛。而麻雀则是没有请柬的嘉宾,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。农人们像极了指挥家,挥动着系了红布条的竹竿,驱赶这些不速之客。麻雀们跳跃于悠长的五线谱间,吟唱着快乐无比的乐章。
如今,每当我品尝那艮硬的白薯干,就像咀嚼一段回味绵长的故事。那被麻雀啄成薄薄一层皮的白薯干,像月牙儿,像小船,飘飘荡荡,载不动农家的几多欢欣、几多忧愁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