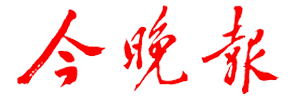老家有个多年不变的传统,除夕那天早晨,要吃粳米粥。几十年前,粳米在北方产量很低,当时一亩地也就产一二百斤,但我们生产队每年总会种一点。到秋天的时候,每人能分得一二斤。这么好的东西,家家都舍不得吃,只有谁生病了,才给做一碗粳米粥。到过年那天早晨吃粳米粥,算是生活里最大的改善。
我的青少年时代,每年只能吃三次肉。第一次是端午节。那时家里再困难,也要想办法找点肉票,买一二斤肉,做顿猪肉炖粉条,让全家人饱餐一顿。第二次是中秋节。中秋时节虽然农事繁忙,但肉还是要吃的。尤其是已经定亲的男女青年,两家都要互相宴请。第三次就是过年了。每个生产队都会杀一两口猪,然后按人头分肉。家庭主妇们则要精打细算,把肉分着用: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炖一点,除夕中午过大年时炖一点,除夕晚上包饺子时用一点,还要留一点正月里待客用。
有一年,我十几岁时,自中秋节过后,几个月都没沾到肉味。我实在馋得受不了,便向母亲要了一元钱,跑到十几里外的县城,花五角钱买了半斤猪头肉。那肉虽然冰凉,但放在嘴里来回嚼,越嚼越香。
那时候,除夕中午的午餐是一年中最丰盛的。除了炖肉,还有熬豆腐、炒饹炸(我们当地的绿豆制品)。鱼是没有的,因为冬天抓不到;虾也是没有的,那时候根本不养。有的人家,会加一盆酸菜——这东西,家家都备着。
我们家,则比别人家多一份特色菜,也是父亲的拿手菜。
我们的父亲,是从来不下厨房的。因为他太忙了,白天要去生产队劳动,晚上回来也不闲着——春夏收拾菜园,秋冬编箩筐、织渔网。只有到了过年这一天,他才会亲自操刀,给我们做一道别人家没有的菜。
父亲洗净手,取一棵白菜,剥去外帮,只留下白菜心。接着,他又把白菜心的小帮剥下来,放在菜板上拍平,然后用刀在菜帮上一下下斜着扁刂。既要扁刂开缝隙,又不能切断。最后,把这些小白菜帮切成一段段寸长的菜条。因为经过扁刂制,菜条形成了齿状,就像一个个弯弯的小锯条。这时候,撒上白糖和醋。因为有这些齿纹,调料都能入味,最终成为一道酸甜清爽、美味可口的凉菜。
吃肉吃腻了,来一口又甜又酸、又爽又脆的锯齿菜心,那滋味,别提多美了。
长大以后,我也学会了这道菜。有时家庭聚餐,免不了挽起袖子露一手。只是孩子们,不太感兴趣,嘟囔着:“都什么年代了,还拿白菜心当凉菜?”
现在每年过年,餐桌上总是摆得满满当当。但大家的吃兴,远没有我们年少时旺盛。父亲的拿手菜,也在时代的进步中渐渐失传,只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