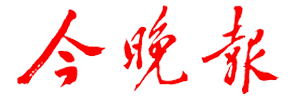整个冬天,我都在心底盼着能与一场雪相拥,但始终未能如愿。
那天,我路过小区的方亭,不经意间瞧见假山池畔的美人梅,正悄然酝藏着一抹胭红,像是藏着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——原来,春的使者早已绕过寒冬的封锁,在枝头投递出第一封花信。
我下意识地伸出手,指腹轻轻摩挲着粗糙的梅枝,那触感,极像儿时老屋墙角的犁铧。那些蛰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,随着岁月的年轮,一圈圈地漫上指尖。立春前夜,父亲总会把犁头擦拭得锃亮,他说,铁器也要晒太阳,要沾染些阳气。今年“春打五九尾”时,我才恍然惊觉,虽然离开老家的土地已四十余载。但骨子里对节气的那份敬畏,从未消散。
晨雾霭霭,含苞的梅朵像是裹着一层轻柔的丝绸襁褓。谚语里说,这样的年景,雨水会很多。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幼时的故乡,我趴在窗台,一颗一颗数着雨滴的时光。那时,檐角的冰溜子总会在惊蛰的前夜悄然消融,化作青瓦上跳跃的溪流。母亲说,这是大地解冻的悄声细语。如今,身处钢筋水泥的丛林,难觅这样的景象。可每当春雨轻叩大地,我还是会下意识地望向案头那抹嫩绿的水培麦苗,这是身居都市的我对土地的不舍与眷恋。
寒潮再次折返的清晨,几朵明艳的红梅,挣脱了鳞苞的束缚。花萼在凛冽的空气中缓缓舒展,这一幕,让我想起故乡那些顶着薄霜,在田间播种的身影。他们微微佝偻的脊背,比任何哲学论著都更深刻地教会我:真正的春天,不在皇历的纸页间,而在冻土下奋力生长的根须里,在顶破冰壳的嫩绿胚芽中,在万物与时光的顽强抗争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