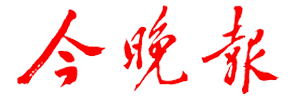“海张五”,原名张锦文,是天津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。时至今日,仍有“海张五修炮台——小事一段”的歇后语流传。在天津著名历史人物中,少有身世像张锦文那样扑朔迷离者。仅仅对“海张五”这个绰号中“海”字的由来,就有“海仁”“觉罗海瑛”等不同的说法,但都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撑。另外,对他依靠盐业发迹的过程,前人所记有不详、不确之处。近日,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数件关于海张五的档案,对以上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。
长芦盐运使的长随
咸丰元年(1851)七月,张锦文被盐商郭逢暤、郭福来父子告至都察院。此案卷宗中留存了张锦文身份的真实信息:“海张五即张锦文,隶籍天津县。”“海张五系前任长芦运司海忠长随,于道光二十三年报捐卫守备职衔。”“在前任运司海忠署内管厨,并管零星银钱出入,系属长随,并非家奴当门丁(看门人)。”由此确定,海张五的“海”字来自于海忠,他的身份是长随。所谓长随,是官宦人家雇用的仆役,并非卖身家奴,可以随时离开雇主。张锦文在海忠手下的职责是管厨、管银钱出入,是天津县人,
海忠是正红旗满洲那丹珠佐领下人,蓝翎侍卫、候补道衔,当过山海关监督、承德知府、热河道等官职。他干得最出色的是承德知府,留下了纂修《承德府志》等政绩,得到了“勤干廉明,听断平允,才优政裕,办事精详,洵为知府中出色之员”的评语。道光十四年(1834)二月,海忠被调到天津署理长芦盐运使。此时正值长芦盐商最艰难的时期,十一月,海忠经不住盐商们请求,向朝廷提交了缓交盐税的建议。道光帝认为他的建议动摇盐务稳定,将他撤职。道光十五年三月,海忠办理完交接后从天津启程回京闲居。道光二十年,海忠被追缴在长芦盐运使任上收受的陋规银两,因为无力缴纳,将自住房产典押,又向亲友借房地产典押,还卖了衣服什物。此后他一病不起,数年后就去世了。所以,海忠并不是个显贵人物。
档案中只说张锦文是海忠的长随,却未说明他是何时、在何种机缘下投效在海忠门下的。前人关于张锦文身世的各种说法中,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年轻时曾远赴沈阳(盛京)地区谋生,依据的都是天津坊间口传。对于张锦文的远徙,只知大致方位而不知其详,所以将承德附会为同属热河的盛京、将知府附会为将军,是极有可能的。由此来看,张锦文似乎在海忠任职于承德时就已是长随了。至于他在此前的经历,档案中并无记载。据《张公建祠志》,张锦文“世居直隶天津府天津县,民籍,家贫少孤,事母至孝”。
如何成为“大盐商”
张锦文盐运使长随身份虽然低微,却是实实在在地插手盐务事宜,而且和上至运使、运同等官员,下至运司署的银匠、书办等胥吏都说得上话。张锦文和运署的门丁、银匠结为盟兄弟,然后利用关系网来牟利。当时长芦盐商疲敝,频繁向盐务衙门求取扶助或宽缓政策,同时大量盐商被参革破产,有数不清的引岸(盐商的专卖区域)、存盐(未能售出的盐)及其他财产、债务、罚银需要处理,盐务衙门的胥吏们大有可操作空间。张锦文从中牟取一些灰色收入,并非不可能。另外,他还经营与盐业有关的席麻等产品,获得了不少利润。
道光二十三年(1843),张锦文捐得一个守备职衔。道光二十五年,他以八千一百两(白银)的代价买入破产盐商潘复兴的房产。道光二十七年,盐商郭松年欠张锦文席麻价银六千两,又以安阳、林县引岸作为抵押,向张锦文借银三千两。可见在这一时期,张锦文已经发家致富,而且资金充裕。安阳、林县两处引岸及其所抵押的债务,后来几经易手到了郭逢暤手中,债务总额提高到了一万余两。十一月,郭逢暤刚刚卖盐完毕,张锦文立即来到安阳、林县引岸,从卖盐银内强行收回欠银七千两,并告诉郭逢暤,来年办运时会再借给他成本银,但当郭逢暤再次向他借银时,被张锦文断然拒绝,郭家因无力缴纳正课及购盐运销,不得不退出了盐业经营。
当月,长芦巡盐御史沈拱宸开始对河南那些无人认领的虚悬引岸实施“捆运”,也就是由官方委派人员,将那些参革盐商被封存的坨盐运往悬岸销售,以避免当地百姓无盐可买以致购买私盐。张锦文受到沈拱宸委派,从天津盐坨领到坨盐五千余包,捆运接济河南二十州县。捆运者虽然要上缴盐利,但由于无需购盐成本且销无定额,因此也是有利可图的,更何况对张锦文这样没做过盐商的人来说,这也是个锻炼盐务的好机会。由此可见,虽然海忠早已卸任,但张锦文在天津的盐务领域早已树大根深,甚至与长芦盐区最高盐务官员巡盐御史的关系也十分密切。
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十二月,清政府决定将河南二十个虚悬引岸全部改行票盐(商人凭政府发给的盐票运销盐,不同于垄断世袭的引盐。)招商领运。商人领运票盐,不像领运引盐那样需要缴纳巨额的引岸窝价银,运盐时也不必履行那些繁琐的手续。票商同样被指定引岸,“如有侵越,即以私论”,已经与引商一样具有垄断专卖性质。为了鼓励商人,清政府甚至允许他们在票商和引商之间自由转换:“若票贩畅行,商欲改票,商有起色,票欲改商,皆可听其自便。”实际上已将票商和引商的界限打破了。张锦文因曾受委派捆运河南引盐,所以水到渠成地进入票商之列,在道光二十九年得到了浚县引岸食盐的销售权。他为自己的票盐生意取字号“义兆霖”,这就是后来张家“益照临”盐店的前身,也是很多官方文件称张锦文为“票商”的原因。此后,张锦文不断扩大经营规模,逐渐成为天津首屈一指的大盐商。
“贱民”身份的阴影
咸丰元年(1851)七月,郭逢暤父子到北京都察院控告张锦文,列出了八项罪状,但大部分都有诬告成分。十一月份案子审结,张锦文因强行将安、林引岸盐价银收入己囊而被坐实了“侵吞帑课”的罪名,被判“杖一百、徒三年”。但都察院判决原借款人郭氏“分作十年归还海张五清款。”这是一个对张锦文十分有利的判决——只要他手里有足够的财富,徒刑、杖责都可以避免。张锦文随后向朝廷缴纳了二万两赎罪银,咸丰帝下旨:“张锦文着准其赎罪。”
郭氏父子的控告虽然并没有让张锦文伤筋动骨,却让他感到极其难堪。他们的指控中有一款是“海张五随姓家奴派充门丁,违例捐纳职衔”,对张锦文的身份发起了攻击。这个指控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《大清会典》明文规定:“四民为良,奴仆及娼优、隶卒为贱,”并且“长随亦与奴仆同。”《清史稿》记载,清朝“官吏俱限身家清白,八旗户下人、汉人家奴、长随不得滥入仕籍”。针对郭氏父子的指控,张锦文辩称自己并非海忠家奴而只是长随,但是即便作为长随,他也不属于朝廷规定的“身家清白”之人,而且这个身份的下贱程度“与奴仆同”,当然没有资格捐职。在最终的判决中,张锦文因“以长随冒捐职衔”而被革去了守备职衔。刚刚用职衔淡化了自己身份屈辱感的张锦文,又灰头土脸地回到了贱民行列。
此后,长随身份成为张锦文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咸丰三年(1853),为了应对北伐太平军,清政府号召官民捐资修造炮位,张锦文以票商身份一次性捐出白银一万两,并且配合清政府协防天津,筑台开壕,捐资练勇。历来盐商有大贡献,朝廷必然会给予议叙奖励。但是吏部尚书柏葰在酌定张锦文奖励时却拿不定主意了,因为他了解到发生在两年前的“郭张控案”,对张锦文的身份起了疑心。于是他向正红旗满洲分旗佐领咨查,后者随即将海忠妻子赵氏关于张锦文并非家奴的保结送来,但柏葰仍然不敢自作主张,于是将此事上奏给咸丰帝“圣裁”。咸丰帝亲下谕旨:“津商张锦文,着赏五品顶戴并花翎。”张锦文依靠巨大的付出,终于又一次脱离了贱籍。实际上张锦文早就预感到身份将会带给他的尴尬。在捐银一万两的同时,他特意递交了一纸呈文,说明自己原有守备职衔被革的原因,以及捐银赎罪的经过,特别强调自己并非家奴,只不过曾经为海忠管理杂务而已。
咸丰帝的谕旨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大臣们不再在乎官员是否“身家清白”。咸丰五年(1855),户部拟定了《推广捐输章程》,试图扩大纳捐范围以弥补军饷不足,其中有一条是“并非契买家人(卖身家奴)准捐虚衔”,“仅系曾充长随之人”,如果捐资助饷至一万两以上者,可赏给五品虚衔,捐资数千两者依次递减给予虚衔。户部之所以敢提出此条,就是以咸丰三年张锦文被赏给五品顶戴作为依据。但是吏部坚持认为“长随虽与家奴不同,究属贱役”,而且其中多有“侵渔婪索”之徒,乃是“奸蠧之尤”,张锦文的破格议叙乃是特例,如果这类人大量进入官员队伍,将会导致贵贱不分,政体混乱,名器败坏,是非常严重的。这些意见得到了咸丰帝和军机大臣的肯定。
事实证明,清廷并没有忘记张锦文的出身,“长随”这个身份将会和“海张五”这个绰号一样,成为张锦文努力想要摆脱的标签。这也许就是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,后来又不计成本地帮助清政府应付英法联军的内在动力。讽刺的是,那个时候,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已经顾不得张锦文的身家是否清白了,从皇帝到大臣一次次给予他赞扬、恩赐,最终赏给他的职衔竟达到了一品,他在天津人和朝廷上下的眼中变成了“尚义可风”的国之柱石。越是如此,张锦文及其后人对他的身世越是讳莫如深,于是其他人便无从探知真相,而只能捕风捉影地猜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