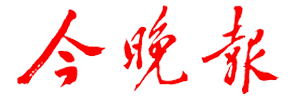朋友告诉我,有一天,在工作的间隙,读到冯至的一首十四行诗——写遥远的威尼斯,想象那个遥远的水城里,“一个寂寞是一座岛,一座座都结成朋友。当你向我拉一拉手,便像一座水上的桥;当你向我笑一笑,便像是对面岛上,忽然开了一扇楼窗”。诗歌的意象算不上特别,却让那一刻的她深陷在“笑一笑”里。因为她心仪的那个人,恰巧就在对面的楼里,于是这首本来具有普遍性的诗歌,变成了她一个人的诗。她反复地读,想象她和他、楼与楼、窗与窗之间的空无,突然漫溢出清澈的水波,她念出的每个音节,都在水上开出一朵洁白的莲花,而她则变成一个纤巧美丽的小人儿,踏着莲花,轻盈地跳到他的桌上,吓他一跳。然后他会向她“笑一笑”,于是桌上那些整齐的、暮气沉沉的文件夹都跳起舞来,而窗外林立的楼群,那一座座卡夫卡式的阴森城堡,突然都变成了童话里的水晶宫殿。
冯至写于1940年代的这组十四行诗,我原本也很熟悉。他写杜甫、鲁迅、歌德、梵高,写鼠曲草的洁白和静默,写村童或农妇的啼哭……战火纷飞中,如他自己所说:“从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到无名的村童,农妇,从远方的千古的名城到山坡上的飞虫小草,从个人的一小段生活到许多人共同的遭遇,凡是和我的生命发生深切的关联的,对于每件事物我都写出一首诗。”
大抵如同苏轼所说的“随物赋形”,诗歌主题的多义性与表达的丰富性,很难一言以蔽之。我从来没有如朋友般,以如此特别的个人情感和童话视角触摸这些诗句,将战争年代的沉重幻化成轻盈甚至俏皮——却并未消解庄重。情深意重,使所有不羁的想象都远离了轻浮与矫饰。
冯至记下这些飘忽的诗思时,大概也不会想到它们会在多年后,将楼宇之间透明的空气,变成活泼泼的春水,而他的诗句,则如同水上的桥,载陌生的读者,通往如童话般美好的彼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