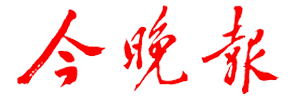上世纪八十年代前,武清乡下的孩子们接触不到竹笋。1981年,我在武清泗村店中学上初中。语文课上,老师讲到“胸有成竹”的成语时,让一位王姓同学站起来做成语解释。王同学结结巴巴支吾半天,忽然说:“胸有成竹就是肚子里有吃下的竹子。”同学们哄堂大笑,语文老师讥讽他:“你肚子里能吃下竹子吗?给我们示范一下?”同学们一笑而过,王同学羞愧难当,竟然转学走了,转到了教学质量更好的城关中学。后来才知道,王同学说肚子里有吃下的竹子也不算错,南方人吃的竹笋不就是竹子吗?只不过那时候的武清农村,吃过竹笋、知道竹笋的人比大熊猫都少,老师也不例外。
因为没吃过竹笋而闹出笑话的,不只是故乡的王同学。晋代陆云《笑林》中有一则故事《北人煮箦》:汉中有个人到吴地去,吴人烧了一锅竹笋招待他,他吃了感觉味道真好,便问这位吴人:“这是什么东西?”吴人回答说:“这是竹子。”此人回到汉中家里后,还想吃笋,便将自家床上的竹席拆下来煮,煮了很长时间都不烂。于是,他就对妻子说:“吴人太会忽悠,竟然这样来欺骗我。”
据说美食家符中士先生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饮食时,经常碰到一件难事:翻译们译不出“竹笋”这个词,只好勉强译成“竹子的嫩芽”或“很嫩的竹子”,以至西方人常常发出“竹子也能吃吗”的疑问。
在中国的《诗经》时代,竹笋就已成为食物。历代写竹笋的诗文浩如烟海,美食大家苏东坡写竹笋的诗流传最广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使人瘦,无竹使人俗。”看来极嗜“东坡肉”的苏轼,在饱餐一顿油腻后,也忘不了竹笋这个“小清新”啊!黄庭坚、李渔、袁枚对用竹笋制作美食都颇有研究。北宋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更是给鲜笋起了个“傍林鲜”的雅号。他主张,食用鲜笋的极致境界在于现采现食,片刻不容耽搁,最好就在竹林之下,以芳香的干竹叶为燃料,跟制作烤红薯一样当场煨烤,才能激活新笋天然的鲜美。身处这般自然恬静的就餐环境,采用返璞归真的烹饪手法,再邀一二雅友共品共饮,此乃人间极致。
前些年,津城的沪杭风味饭店里流行一道手剥笋凉菜,选细嫩如玉指的细笋,宽水沸煮,仅用盐和花椒简单调味,清口食用,便觉将春天的至鲜尽数收入口中。然而,若与“傍林鲜”相比,这道手剥笋便相形见绌。有些北方人吃这道手剥笋时,竟要蘸上芝麻酱,如同吃麻辣烫一般,这般重口味,若被林洪知晓,恐怕他那口好牙都要笑掉,碎落满地了。
在南方,相对于冬笋,春笋更是家喻户晓。因为冬笋深藏地下,挖掘需要一定的技术,得之不易,采春笋就简单多了。俗话说:“清明一尺,谷雨一丈。”说的是在清明谷雨前后,竹笋生长旺盛期的惊人速度。若是赶上春雨,那遍地春笋就在一夜之间轰然破土而出,只管扛着锄头去竹林挖掘就行。
春笋清脆、润泽、肥腴,清代李渔用“肥羊嫩豕,何足比肩”来赞美春笋超越羊肉和猪肉的鲜美。油焖春笋是江南人饭碗里必不可缺的时令佳肴,做法也不复杂。春笋切厚实大块焯水,用当地农家当年榨的菜籽油,加酱油长久焖煮即可。一款看似灰头土脸却内藏乾坤的土菜,就将春笋的肥嫩无限放大,真没辜负了春天里这独有的盘中尤物。
大画家吴昌硕曾在自己的画作上题诗:客中常有八珍尝,哪及山家野笋香。
好一个山家野笋香,真让人垂涎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