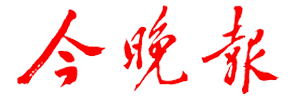小时候,一到年关,天气就嘎嘎冷。
我们这群小孩,每当时光进入腊月,就日日盼着老天快点下雪,快点冷起来,快点来到过年的时刻。我们在天寒地冻中迎来了年,心中充满无穷的快乐,并且总是幼稚地认为,年是被寒冷“冻”出来的,年是被大西北风“刮”过来的。我们不惧怕寒冷,是因为心里有个热烈的盼头——过年能穿新衣服,能有好嚼咕(东北方言,好吃的)吃。盼年,成为我们抵御寒冷的勇气。在幼小的心灵里,“年”与“冷”的天平,更倾向于前者——我们觉得“年”比“冷”重要。这份对年的期盼,也增添了克服寒冷的信心。只要有“年”过,冷点又算什么?
记得那是一个大冷天,我到井沿拉冰块,准备在窗台下冻猪肉。当时,我穿着小棉袄,里面还没穿衬衣,冷风从袖口、扣缝嗖嗖地往里灌,但我并不觉得冷,因为心里装着一个“暖火盆”,那是家里正杀年猪的热乎劲儿。铁锅里炖着的杀猪菜咕嘟冒泡,香味混着雪花飘出老远,连村道上都是肉香裹着冷意的气息。
每当“腊七腊八,冻掉下巴”的日子,母亲便一锅一锅地蒸黏豆包,蒸好后又一帘一帘地摆好,放到仓子里冻上。母亲常说,豆包冻透了,年味儿才香。那刚出锅的黏豆包,冒着腾腾的热气,被裹进寒冷的空气里;一个个小豆包,宛如寒冬里最温暖的弹弓球子,打透了寒冷的“十环”,直抵人心。
每当临近过年,一到天黑,我们一帮小孩子就手提小蜡灯,满屯子乱跑乱串。那灯笼里的小火苗,在寒风里颤巍巍地跳跃着,昏黄的光竟也冻得格外清亮,把雪地里歪歪扭扭的小脚印,都照得真真切切。
小时候过年,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糖块。每当冬腊月,母亲都会熬些甜菜疙瘩糖稀,做成大块糖,端到仓子里冻上。等糖块冻得硬邦邦的,吃到嘴里,冰凉又嘣脆。有时地上掉了几个碎渣,我也舍不得浪费,捡起来就塞进嘴里。虽有土腥味,但甜意不减,仍能从舌尖漫开,一直钻到心底。
年,是“馋人”的节日。每当老天落雪了,天气冷下来之后,我就被无形无影的年给馋得迷了魔了的。一有闲空,我就反复琢磨,年肯定是冻出来的,要不怎么天气越冷,年味儿就会越浓呢。说起来,冷的功能很奇妙,它冻出了杀猪菜的香味,冻亮了小蜡灯的明亮,也把我365天的盼头,冻成了甜滋滋的美好和未来。
如今每到年关,我仍然会想起儿时“冷”与“年”的往事,眼前也总是浮现那些把手冻得通红、把对联冻得通红、把小蜡灯冻得通红、把日子冻得通红的时节。原来,年果真是冻出来的,它冻在黏豆包里,冻在猪肉里,冻在福字里,凝结在我童年鲜活的记忆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