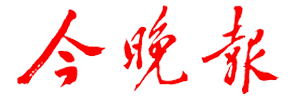上周日清晨,寒风凛冽。我匆匆跑进社区活动室时,心里却蓦地一沉:光顾着高兴来参加剪窗花活动,竟把装剪刀和红纸的手提袋忘在了家里的玄关。
活动室里坐满了人,每人面前都铺着红纸,回家取已来不及,我僵在座位上。“闺女,怎么啦?”身旁一位牵着孙子的银发奶奶温和地侧身问。听我说明缘由,她笑了,眼角的皱纹舒展成慈祥的弧度:“你用我孙子的这份吧,我和他用一套就行。”说着,便取出剪刀和红纸递到我面前。
可一动手我就露了怯。剪刀在转折处不听使唤,手腕僵硬。本想剪一枝梅花,该圆润的花瓣却剪出了锯齿,纸边毛糙,碎纸屑洒了一桌。奶奶的小孙子看着我,捂着嘴直笑,我的脸颊顿时烧了起来,心里更添几分慌乱。
正不知所措时,一只温暖的手轻轻覆上我的手背,奶奶俯身靠近,身上带着淡淡的皂角清香。“手腕定住,让纸转。”她的声音低而稳,引着我的手,那个僵硬的拐角竟化作一道流畅的弧线。剪刀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忽然像有了韵律。
我屏住呼吸,跟随她的节奏,她教我用指甲在纸上压出折痕作为引导。“剪纸急不得,心静了,手就稳了。”她轻声说着,慢慢松开手。几次尝试后,在某个瞬间,我忽然抓住了那种“转动纸张”的感觉。
活动接近尾声时,我竟完成了一幅虽不完美却姿态生动的梅花窗花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,穿透薄薄的红纸,在桌面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影。
“奶奶,这个送给您。”我鼓起勇气递过去。她却将我的手轻轻推回:“这是你亲手做的第一幅,该自己好好留着。”她顿了顿,语气柔和,“剪纸啊,工具和纸是死的,可手心焐过的温度,纸会记得,剪刀也会记得。”
我从工作人员和奶奶的交谈中得知,奶奶年轻时便是远近闻名的剪纸艺人,这些年她常来参加活动,却从来不主动提及自己的过往。
回到家,我把那幅梅花贴在了书房窗前。每当目光掠过,便会想起那双覆在我手背上、布满岁月痕迹却无比安稳的手,想起她说的“手心焐过的温度”。或许,传承就是这样发生的——一个人将自己手心里那点细微的暖意,连同对一门手艺的全部虔诚,静静地渡到另一个人的掌心。
而那一页单薄的红纸,从此开始,便有了两种温度,也叠合了两段时光的柔光。
指导教师:展淑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