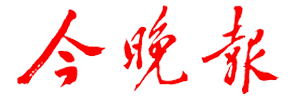独居的张大爷不爱说话。做了这么多年邻居,见面和他打招呼,他也只点点头。只有在喝酒后,他的语言开关才稍微敞开一溜缝儿——他出来送客,爱说“慢走”——关系普通的,说一句“慢走”;关系近点的,说两次;要是开口说四句“慢走”,那肯定是大年初五,他的老同学来了。
只有过年那几天,他家才热闹起来。初一到初四是同族晚辈和亲戚来拜年,初五则是老同学来访。他有位老同学,初五这天准骑着自行车、带着礼物来看他。这一天,张大爷早早就要出门张望好几回。等到他家飘出炒鸡蛋的香味,就知道老同学已经落座了。张大爷不会做饭,唯一拿手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。儿女年前就把年货备齐了,他切几盘卤肉摆上,再亲自下厨炒个热菜——西红柿鸡蛋,下酒菜就有了。
一对老同学边聊边喝,直到下午三四点钟,便会听见他出门送客。“慢走”说了四遍,大门才缓缓关上。第二天,张大爷一大早就把礼品捆在自行车后座上,出门去了,下午天擦黑才带着点微醺回来——不用问,是回访老同学去了。
有年初五,没闻到炒鸡蛋的味儿,也没听见一句“慢走”。后来才知道,那位年年来看他的老同学,头年秋天去世了。那个春节,张大爷又沉默了,连我的年也过得有些寡淡。
前年腊月,本家一位叔叔托我打听张大爷的手机号——叔叔的岳父的邻居的亲戚,是张大爷的小学同学,周转多人打听张大爷的联系方式。张大爷很激动,赶紧把手机号抄给我,请我转交。
失联已久的老同学就这样联系上了。初五那天,张大爷又出来好几趟等着迎接老同学。十点多,人接到了。自行车声伴着他响亮的大嗓门:“六十多年没见啦,今天可得好好喝两盅!”不出一个小时,炒鸡蛋的香味就飘了出来。下午四点左右,“慢走”的声音穿过窗户传进我的耳朵。一连三声之后,却没等来第四句。“不对呀,怎么少了一句?”我扒着窗户朝外看。“肯定得多送一程。”母亲猜得没错。半小时之后,有人唱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……”张大爷哼着戏回来了。这一程送得可真不近。第二天,我没听见他自行车的动静。母亲说:“你起床都快九点了,老张不到八点就驮着两箱礼出门啦。”
每年“偷看”张大爷会见老同学,成了我过年的保留节目。八十多岁,还能骑自行车出远门拜年,而且像我们小时候那样,带着礼物,非得在人家吃饭喝酒——双方那种藏不住的喜悦,才是真正的“古法”年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