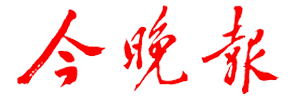一夜乱梦,全都是雪。
闹铃一响,我顾不得披上睡衣,赤脚冲到窗前,一把拉开窗帘。窗外依旧是熟悉的灰蓝色天空,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摇晃,不见一丝雪的痕迹。嘿,又空等一场。我悻悻然钻回被窝,想再眯一会儿,想把梦里那片白续上。
刚要合眼,“哒哒哒”的拖鞋声由远及近。儿子一路小跑着钻进被窝,搂着我的脖子问:“妈妈,下雪了吗?可以打雪仗了吧?”我苦笑:“打不成咯,雪还没下。”他一下子蔫了,趴在我怀里嘟囔:“怎么又没下,我都等好几天了。”他那点失望,像根针轻轻刺了我一下,而梦里那铺天盖地的白,却在脑海中愈发清晰。
思绪滑过那片虚幻的雪景,一路飘回五年前冬天的那场大雪。
那雪下了一天一夜,积起来的雪映得屋里亮堂堂的,却未能照亮我心底的暗沉。雪下最猛的时候,医院的电话来了,医生的话字字如雷:“报告出来了,确诊是甲状腺乳头状癌,建议尽快手术。”窗外的雪还在纷纷扬扬地飘,而我的世界,在那一刻已然坍塌。铺天盖地的白,不再是浪漫的景致,成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苍茫。
挂了电话,我呆坐着,眼泪无声地往下掉。爱人默默坐到身边,紧紧握住我的手。他的手心也是凉的,却那样用力地握着,仿佛要把所有的温度都传递给我。
父亲开着那辆旧皮卡送我们去高铁站。车厢里没有暖气,他握方向盘的手冻得通红。十几公里的路程,寒气直往骨缝里钻,可这份冷,远不及心底的寒意。爱人把我的手揣进他怀里暖着,我依然止不住地轻颤。那种从心底蔓延开的恐惧,就像窗外的大雪,无孔不入,无处可逃。
……
思绪回拢时,我下意识望向窗外,不知何时,竟已飘起了雪花。我轻轻推了推儿子:“快看,下雪了。”他一下子弹坐起来,扒着窗户欢叫。
雪花渐渐密了,细碎的雪片在风中静静旋舞。术后五年,每次复查都很好,生活也早已回到原有的轨道。五年前的雪,曾几乎压垮我的世界,而此刻的雪,正轻轻落在儿子雀跃的心尖上。他忽然转过脸来,眼睛亮晶晶的:“妈妈,雪再下大点,明天就能堆雪人了吧?”我点点头,把他搂得更紧些。
或许,每场雪都有自己的时节。该来的总会来,该化的,也终会化去。明天,待雪积厚了,我要握一团清凉的雪,轻轻放进他温热的小手里。
何迎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