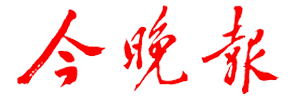作家孙犁回忆自己的母亲。
他写道:“1956年,我在天津,得了大病,要到外地疗养。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,当我走出屋来,她站在廊子里,对我说:别人病了往家里走,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!”
读到这里,心里一震。有人拆字,把“家”字解释为一口屋子一头猪,意为有立锥之地、也有些许薄产,即可称之为家。我倒始终觉得,所谓家,其实是个有念想、有牵挂的地方。有牵挂,才有回乡的必要。不然,回去何为?
家有老母亲在,千里万里、魂里梦里,总是要回去的。
我幼年丧母。16岁考上师范离乡,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。外出上学那一年,祖母已经82岁。每到周六,白发苍苍的她总要到村口锯木厂外的路口等我。彼时,她年事已高,即便拄着拐棍,也走不了多远。她是旧时代的大家闺秀,裹着粽子般的小脚来回奔波。久候我不至,她便坐在路边的青石堆上,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有时天黑了,见我还没有回家,才失望地走回去。
这,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。
孙犁母亲那句“病了往家走”,着实说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在亲人眼里,一个人出门在外,活得是否光鲜并不重要。平安与健康,才是令他们时刻牵挂的。
所谓“家”,大约是这样的:当你累了、痛了、病了、厌倦了,可以随时原路返回,随时选择躺平并休养生息。
家,就是一张大弓,把你从那个低矮的小院子里射出去,看着你开枝散叶,落地生根。也看着你快乐或者压抑,萌发或者张扬,愉悦或者痛苦。
一朝混得狼狈了,家是唯一的归路。它,可以保证你回去有饭吃,可以接受你的失败与平庸。
满世界流浪找不到归途的,才是丧家之犬。
你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