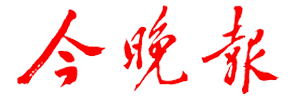一位要好的朋友去了遥远的国度。
原本,我每天上下班,都会路过她家。她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六楼租了小小的一室一厅。她少年时早早离乡,这些年辗转多地,是新时代全方位的独立女性——经济、情感、日常生活。传统家庭中那些依赖男性的力气活儿、技术活儿,她都以自己瘦弱的身躯独自完成。她的家里常备各种各样的工具,似乎什么都能修。租下这个小小的居室后,她自己装窗帘,换灯,用一个简易但结实的梯子爬上爬下,如履平地,镇定从容。她用一些简单的装饰,让这个独居之地有了家的温馨与她独特的印记。我有时会到她那里坐一坐,不需要事先打招呼——只是在她那张餐桌兼书桌旁的木头椅子上坐一坐,就能感受到一种难得的轻松和安心,简单的居室,竟似有明月松间照,有清泉石上流。
她离开后,那间屋子暂时空了下来,应该还没有新主人入住。有时候很晚了,我经过那里,抬头看看那扇窗——黑的。
据汪曾祺回忆,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教他们写作,曾经布置过一个奇怪的作文题:记一间屋子的空气。我借用这个作文题,想象那间我们曾经那么熟悉的屋子的空气。它们静默无声,慢慢有了尘土的味道、寂寞的味道、思念的味道。它们透明无色,随日光、月光、对面楼群的灯光而变。我们曾一起讨论中英文的翻译,对一段英文的中译本印象深刻:“浮世三千,吾爱有三,日、月与卿。日为朝,月为暮,卿为朝朝暮暮。”突然想到,那段抒写爱情的文字,如果借用来对着那间屋子里的空气歌唱:“日为朝,月为暮,卿为朝朝暮暮。”倒也不失为奇思妙想。不知道写下了澄澈到近乎透明的《边城》式爱情的沈从文,会如何评价这样奇怪的嫁接?
还曾在一篇小说里读到过这样的细节:一个女人在深爱的男人曾经居住的房间里久久徘徊,发现窗台上有一瓶矿泉水——喝了一半。男人离开很久了,所以这瓶子也搁了很久了。她情不自禁,旋开瓶盖,喝了一口。那水带着一点奇怪的生锈的气味——也许是她的心理作用,流经她有些干涩疼痛的喉咙,她竟有清露润喉之感。她终于从持续了很久很久的痛苦中挣脱出来,蹲在地上,号啕大哭。
小说就此戛然而止。而我却闭上眼睛开始想象,那间屋子的空气,凝结为一块硕大而美丽的白水晶,将瘦弱憔悴的她囚禁其中。而她的哭声,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让水晶碎裂,落了一地。她从一地的碎片中站起身来,打开关闭了很久的窗——窗外,是一个世界的空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