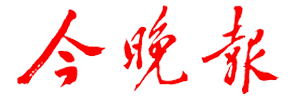在开始阅读小说《平原》之前,我们似乎有必要大致了解一下本书作者杰拉尔德·默南的人生经历。这位澳大利亚作家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隐士。在86年的人生中,他几乎从未离开居住多年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,更别提乘坐飞机环游世界。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己的方式想象远方的风景。因为所有那些令人惊叹的景致都被他完好如初地保存在记忆深处。于是,写作就成了某种程度的自省。就像默南所说:“我的小说是我的内心写照。我不会试图让读者相信我的作品向他们展示了现实世界,无论它是什么。我的书是以我内心的风景为背景的。”
毫无疑问,《平原》就是这样一种想象的产物。小说开篇,叙述者“我”独自待在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一个被称为“平原”的地方,如此缓慢而又持续地回想起自己20年前初到此地的情形。在“我”的描述中,这是一次奇异的远行。彼时,身为艺术家的“我”带着一部名为《内陆》的电影笔记,辗转来到位于内陆深处的平原,想要寻找合适的赞助人与取景地,却不料竟然见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和事。
这里有太多用白色挡风板搭建而成的、占地宽广的大房子,“屋顶则由刷着红漆的铁板组成,巨大的旱地花园里长满了胡椒树、异叶瓶树和成排的怪柳”。不仅如此,这些自称为“平原人”的居民也有着与别处截然不同的审美。“他们都穿着平原上有教养的有闲阶层的服饰——裤线笔直的素灰色西裤,一尘不染的白衬衫,上面还配着相称的领带夹和袖章。”
而“我”呢?尽管“我”每天都坐在酒店里,与不同的平原人相互交谈、一起喝酒,暗自揣测他们的所思所想,但“我”的服饰打扮却透露出“我”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观光客。“我”穿着白衬衫,敞开的领口上系着一条深红色的佩斯利花纹丝绸领巾。不幸的是,平原人几乎不系领巾。好在,“我”终究还是把握住了平原人隐秘的喜好。“我”的左手上戴着两枚饰戒,“每枚戒指上都镶嵌着一块显眼的半宝石,一块是朦胧的蓝绿色,另一块是柔和的黄色”。
两种颜色恰到好处地呼应着平原人矛盾的性格特征——既渴慕远方遥远的地平线(海水是蓝绿色的),又不忘身边的大地(泥土是暗黄色的)。或许正是凭借着如此精准的判断,“我”最终还是被平原人接纳了。从此,“我”正式开启了“我”的平原人生。但奇怪的是,“我”并没有完成“我”的电影笔记,却把时间耗费在庄园的图书馆里。每一天,“我”都会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,仔细研读平原地区的历史,并试着从中探求平原人的精神状态。
毋庸置疑,这就是典型的默南式写作。他从来不愿为读者提供任何令人眼前一亮的情节,却总是用他冷静而又克制的语调谈论一些相似的话题:它们在平平淡淡中展开,最终又在平平淡淡中结束,就像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。但我们不必因此责怪默南。因为这就是他对“平原”这一主题的设定。正如他所说,平原人从不在意通常意义上的故事,更不会“被情感的迸发、激烈的冲突或突发的灾难所打动。他们认为,呈现这类事物的艺术家不过是被人群的嘈杂声,或被平原之外的那个世界,那个被透视法缩小了的世界里过于丰富的表象迷惑了”。
似乎是为了摆脱被外面那个世界“过于丰富的表象”迷惑的恶果,默南轻易地抛开所有寻常的故事情节,以他标志性的敏锐,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被暗藏在看似平淡的地标(“平原”)之下的微小细节。因为平原人总是会“在一片单调的土地上,从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塑造出神话的实质”。想象这样一幅画面:某个平原人的英雄“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每天下午回到不起眼的家中,房子的草坪平整、灌木萎蔫,他会一直在家坐到深夜,试图决定一条他可以沿着走三十年的旅行路线,那条路线最终将抵达他坐着的地方”。或许,这就是默南最擅长的旅行,也是他最熟悉的澳大利亚。而这一次,他迂回辗转,持续前行,最终抵达了这片位于他内心深处的土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