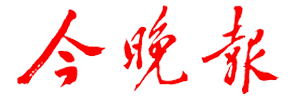腊月十五左右,村子就醒了。家家户户开始忙一件大事——蒸馒头。多的用三四百斤面,少的也要两三百斤。全村唯一的大蒸笼日夜不停地转,成了腊月里最忙的物件。
“王猫糕”是我们老家对一种长条馒头的叫法,因形似黄鼠狼(乡人称“王猫”)而得名。它是刻在味蕾上的故乡印记,是年味里最扎实的一笔。
蒸馒头那天,几口大缸挨墙排开,半截埋在软茅草里。掌酵师傅一早就来“掺酵”:面粉入缸,加水,加酵饼泡开的水,反复揉按摔打。老酵馒头的魂,全在这揉面的功夫里——劲要匀,力要透,面团才会活。
掺好的面团放入大缸,上锅盖,裹棉被,静静等着。三四个钟头后,师傅不时揭开缸盖,用手背试试温度,用眼睛量量发酵的火候。发过了,馒头酸;发不够,馒头黏。老人们说,一笼馒头蒸得好坏,连着来年的运道。
面团涨到缸口时,师傅点点头:“可以做了。”大家便围上来,扯面,整形,一层层摆进蒸笼。十层笼屉坐稳大锅,灶膛里燃起旺火。烧的是耐燃的硬柴,火要稳,气要足。
三四十分钟后,白汽弥漫了整个灶间。师傅揭开顶盖看一眼:“出笼。”孩子们早就等急了。馒头倒在院里的芦苇帘上,麦香混着酵香随着热气扑来——那是过年才有的,让人安心的香味。
心急的娃娃不怕烫,掰一块就吃。馒头微黄,气孔舒展,咬下去韧韧的、筋筋的。简单的麦香在嘴里化开,却是最扎实的满足。当家人尝过后露出笑意,这年才算有了底气。
那是黄海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腊月图景。如今村里很少有人自家蒸馒头了,但走乡串巷卖“王猫糕”的还有。有的仍用老法子慢慢发,有的图快,用了酵母。模样虽在,味道终究淡了,少了那份浑厚的魂魄。
每次回乡,只要遇见,我总不忘买上一两条。碰上正宗老酵做的,咬下去的刹那,童年的腊月便回来了——满屋的蒸汽,灶膛的火光,还有空气里那份稳稳的幸福。现在好吃的再多,也代替不了这一口朴实的念想。它不单是食物,更像一把钥匙,轻轻一转,就打开了岁月里那扇温暖的门。